公德榜 诗歌词赋 杨氏企业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西 广东 海南 湖南 湖北 江西 福建 四川 贵州 云南 浙江 江苏 河南 安徽 陕西 山西 山东 河北 辽宁 吉林 甘肃 青海 台湾 香港 澳门 新疆 宁夏 西藏 海外 黑龙江 内蒙古 |
杨卫 1954年生,湖南浏阳人;1976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锻压专业;固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浙江大学校长等职;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研究微/纳米力学,断裂力学与本构理论,智能材料与结构的力学,航空航天结构与材料等;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奖章、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以及“国家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身材魁梧、面容和善的杨卫今年已届花甲,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当过知青、教授、名牌大学校长,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负责学位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从专家教授到国家学术机构的高层领导,一路走来,杨卫以扎实的功底、宽广的视野、超人的睿智和卓越的管理能力而为人们所称道。
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杨卫在西北工业大学材料与热加工系锻压专业度过了他难忘的大学本科时光,开启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为他成为优秀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轻的院士】
杨卫1954年出生在北京清华大学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杨光华是1951年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石油系主任、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石油大学校长等职务;母亲孙以实曾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教授。杨卫是北京清华大学附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插队的那年他14岁,因为年龄太小,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说服父母和老师走“后门”办齐了插队手续并登上了知青专列,1969年1月20日来到了陕西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插队落户。早在杨卫提出上山下乡的时候,父母就要求他到农村不要放弃学习。因此杨卫利用劳动之余在土窑洞里昏暗的煤油灯下自学完成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1976年底杨卫从西工大毕业之后,主动要求去江西上饶地区景波机械厂工作,担任工艺员,并在当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1978年杨卫调回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当了教师。在清华大学对三百多名青年教师的一次考核中,他取得了数学、外语两项第一的佳绩。不久清华大学开始招收“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杨卫改换专业后在百余名竞争者中名列第四。1981年研究生毕业,他又作为清华大学的公费生前往美国布朗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学习。1984年末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完全有能力留在美国工作的杨卫,放弃了高薪,依然回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担任讲师,随后被评为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
作为我国年轻一代的固体力学专家教授,杨卫在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工作了26年,担任过工程力学系主任、航天航空学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长期从事断裂力学、细观与纳米力学、力电耦合失效等领域的研究,参加并主持了众多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黄克智和清华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所长方岱宁,一个是杨卫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一个是多年学术团队的副手。以这三人为核心完成的“铁电陶瓷的力耦合失效与本构关系”项目,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荣获200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杨卫选择的都是国际前沿课题,不止在国内是第一个开始做,和国际学术动态也始终保持同步。”黄克智和方岱宁都这样评价他。
“杨卫在学术界的人缘、威望都很好,对学生也很和善,懂得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作为研究副手的方岱宁说自己得到了杨卫的很多帮助。而杨卫的几个学生,如今也成为了力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他治学是很严谨的。”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副院长仲政回忆,杨卫身为导师,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在写博士论文时,杨卫从内容到文字甚至英文拼写,都改得很仔细,最后整篇论文,杨卫共改了七八遍。
在校期间,杨卫多次作为邀请学者和客座教授赴美、英、法、加拿大等国进行研究和讲学,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称赞,并收入美国传记研究院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杨卫曾10多次获得国内外重大奖项,其中包括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全国优秀教师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不满50岁。
杨卫工作以严谨高效著称,但与其他专家学者和高层管理人员不同的是,他很会“玩”,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新潮”。他爱看电影,口味很宽,从美国大片到伯格曼的作品,这是80年代留美时养成的爱好。和他聊热映影片,他基本一部不落。他也爱看通俗小说、反映政治的历史小说、军旅小说等。“工作的时候效率高,玩的时候也会玩,做什么都很投入。”这是杨卫周围的人对他的普遍评价。
【力争做成功校长】
2004年夏天,杨卫在家中接到了教育部部长周济的电话,对他说了要将他调任教育部的事。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是一个新机构。2004年1月,教育部设立该司,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杨卫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正式步入国家教育高层管理机构,开启了他的管理生涯。他主要负责对学位点、重点学科、211工程和985工程项目、全国优博评审等工作。
2006年8月,杨卫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当时正值中国高校领导换届高峰,而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是当年第十所更换了校长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杨卫和许多新任的高校校长一样,有着海外留学和政府官员背景。
“我虽然主要生活在北方,但也和在座的许多浙江大学的老师和领导们一样,与浙江大学有着不解之缘。”杨卫第一次亮相,就细数了自己和浙大的渊源:父亲杨光华1941年到1945年是浙大的本科生,抗战后曾留校任教。杨卫的儿子杨越,2000年到2004年在浙江大学就读。“今天我到浙江大学与同志们一起工作,我们家祖孙三代的浙大之缘终于圆满了。”杨卫说。
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大学和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成为最热点的社会话题,其中的问题和弊端正经受着来自社会各方力量的关注和批判。
大学校长的角色变得尴尬起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个象牙之塔里的学者,一个由上级任命的官员,原来主要对上级负责,如今却要面对社会的问责,并且,随着传媒的日益发达,高校里的知识分子也越发强调自己的独立立场,借助公共平台,批评现行制度和高校管理体制。
杨卫说:“做好一个校长很不容易,大学教育是教育链的最高端,而大学本身又是一个教育链,比如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等等。大学有自己的规律,首先是教书育人的规律,主要是如何培养人、塑造人,其次,是大学发展的规律,你在大学的前进中要享受这个发展的过程。”
“作为一名校长,不仅应该是教育管理者,是教育家,还应该是学者,在某一个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还是一个CEO,是一个战略家(在社会期盼的重要问题上发表见解)。同时,按照中央的要求,大学校长还应该是一个政治家,应该从国家发展的高度、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培育人才。”
杨卫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摊子——1998年四校合并以来,浙江大学拥有5个校区,在校生人数多达几万。幸运的是,在广受质疑的中国高校“合并运动”中,是个拿得出来的正面“典型”——合并之后,处于上升趋势,无论报考学生质量、科研经费,还是全国重点学科评选,均处于上升趋势。
上任伊始,新校长抛出了浙大应是“江南名校之首”的概念,尔后在一个小型场合,又谈到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浙大要追求更卓越。两番言论,让浙大的师生兴奋不已。
新官的“三把火”,他绝口不提。他表示认同前任校长定下的目标——一个是冲进一流大学的10年时间表,另一个是把浙大办成“综合性、研究性和创新性的大学”。
“首要的,是让不同学科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我们的目标是建立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在人文、社科、理、工、农、医这些大类里,最起码要有一个或多个拳头学科。”杨卫说。
从学科排名上来评价,综合效应已经很显著,“之前相对弱一些的如医科、文科和理科,这几年发展得比较快。在2007年的全国重点学科评选中,浙大由过去的24个到现在的48个,翻了一倍”。
杨卫的言谈中鲜见人文思想、大学精神这些抽象概念。他更倾向于用数据量度学校的现状,用指标构筑未来。他构想中的另一个目标——浙大要成为中国金字塔尖的研究型大学,也是由各项指标构筑而成。“希望浙大能有一批学科成为世界知名、进而一流的学科。在总研究经费上,经过购买力修正之后,浙大的目标是要进入世界前百位”。
在浙大,杨卫校长提出并努力践行“三个爱”,即:爱学生,爱教师,爱学校。杨卫说:“爱学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比如,你不能怕学生,也不能烦学生,要有各种机会和学生交流,要设身处地为学生考虑,当然,这个不是说你要去迁就学生。”
“我经常去学生食堂吃饭,这个食堂是学生、教师在一块儿的,食堂很挤,有时座位也很难找。当然,这个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杨卫笑着说,“只有你经常去吃了,才知道菜贵不贵,口味好不好,就‘接地气’了,学生看到你也很亲切。”
作为校长,杨卫在每年开学的时候,都要给新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始业教育”,杨卫自己讲,一般要讲两三个小时,“对于本科生,主要是介绍学校的情况,对于研究生,主要讲讲学术生态。每次讲完,还要与学生进行互动,效果不错。”
每年,校长要和每一位获得证书的毕业生握手,春夏两次,合计要握一万次手,握手握得肩膀上的肌肉都酸痛了。还要合影,10人一张,拍1000张照片。每年用2天时间做这个事情,即便很辛苦,杨卫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对于浙大学子而言,留在心中的记忆是美好的。
因为经常在学生中走动,上学生食堂吃饭,给学生作报告,还握手拍照留念,等等,所以,浙大学子都认识他们的校长,杨卫开玩笑,“我走到哪里都会碰到学生,他们都认识我。”
爱教师要包容,为他们发展提供好资源,彰显其个性。
“浙大的教师都很有个性,很有批评精神。”对于爱教师的话题,杨卫是这样开头的。
“来浙大不久,有一次开座谈会,结果很多文科教师对学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杨卫说,“我们很多教师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学校的情况有了解比较深的地方,也有不太了解的地方,信息不对称。”
后来,杨卫每年都组织文科教师的座谈沟通会,一开始是人文学院(文史哲)的教师代表参加,后来,不断有老师要求参加座谈,于是便“扩编”到人文学部(还包括外语、传媒等)了。
“更重要的是,在学术上,要历尽所能,帮助老师探索道路,为教师提供学术平台。”杨卫说,“校长不能简单看作是教师的管理者,要为教师的发展提供更好的资源,让教师彰显个性,共同发展。”
说到爱学校,“就是要为浙江大学的发展而努力,与浙大干部、教师、学生同呼吸,共命运”。
杨卫主政浙大期间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即“大学是有生命的”。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我应邀去参加哈佛大学的校长换届典礼。典礼入场式上,来自全世界各大学的校长按照建校时间入场,历史悠久者为先。那时,浙江大学已经建校110周年,但是,在几百人的入场队伍中,浙大依然排在尾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全世界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是很多的,大学的生命是很长的。从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即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到现在,已经900余年。相比较于人的寿命来说,显然要长很多,而且,即使是长达几百年历史的大学也并没有进入暮年之势。纵观世界,越著名的高校往往历史越悠久。
而大学之所以能这样繁衍发展、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大学如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一样,能不断接纳创造新的学科、思想与精神。
杨卫说,首先,管理大学同管理企业是不同的。相比较于企业来说,大学的生命更长,这就要求大学的管理和制度建立不能以一年为周期,要以大学成长发展的规律来确定,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为一个周期,不能搞短期行为,大学的管理者要有长远的目光和目标。具体来说,企业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大学不能以招收更多的学生、争取更多的经费、出更多的论文为目标。如果是这样,大学一定会形成一个浮躁的氛围,而缺乏责任感与使命感,缺乏十年磨一剑的踏实氛围。与之相关的,大学还需要一个健康、科学的评价机制,要求我们对于一位学者的判断,不能完全按照客观定量的指标来看,而是应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进行总体与科学的评价。
其次,是我们中国高校的特色,是党委和行政双重管理模式。杨卫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比喻成人体DNA的双螺旋结构,彼此信息沟通,缠绕上升,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作为国内顶尖大学,杨卫强调:“要享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他认为大学应该以十年为自身的年度单位。那么,牛津、剑桥大学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也就只是八九十岁,我们中国的高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实,也就才十一二岁,还很年轻。
同时,人体有新陈代谢,大学也是如此。教师在大学的工作时间一般为20-40年,如30岁开始,任教到60岁。一所大学,一般情况下,大约十年增加更替1/3的新鲜血液,再考虑到文化自身的延续性等缘故,对一所大学来说,十年可以出现显著变化,但是一定很难出现脱胎换骨的变化。这就说明,用十年的时间从世界二流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不太可能。尤其是在我们目前高校的师资水平同世界一流大学师资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的前提下,用十年的时间赶上世界一流大学很难。
当然,要强调的是,尽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会很漫长,我们不能因此而不作为,相反,应更加有所作为,而且,必须要有强烈的信念支撑与精神的支柱。因为,如果甘居二流,最好的学生与师资就会离你远去,这无异于慢性自杀。
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有目标,清楚地知道实现目标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也不能将其看成很苦很累的过程,要逐年寻求进步,并享受这个进步的过程。
【自然科学基金“掌门人”】
杨卫说,从国家发展来看,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实现中国梦,过程上是由“大”变“强”,先成为经济强国,再到技术强国,但这样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成为科学和文化的强国。目前中国在信息、制造业、交通运输等应用技术领域已经逐步起飞,但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有些差距。随着逐步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基础研究在今后20年到30年将会有一个全面兴起的势头。为了那个时候的早日来临,我们需要早做准备,对源头的、基础的科学领域给予足够的支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激发科技人员原始创新的想法和热情。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今后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杨卫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必须把握国家十分重视基础研究的重大机遇,对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进行深度的战略研究。梳理科学发展、学科延伸的脉络,深度研究新兴学科的地貌图和我国基础科学学者的配置结构。要加强对科学基金整体性、一致性、共同性的探讨,拓展我们基金资助的新边疆。同时,要编织好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的联系纽带。要从基础研究的视角上,观察并应对人类和中华民族发展的若干重大科技挑战。要探讨与相关部门及产业科研群的共同资助方式,拓展中国知识链、教育链和创新链的长度和相互缠绕度,建立可冲击这些Grand Challenges的双赢机制和平台模式,资助旨在建设大科学平台的设备体系架构。
杨卫满怀信心地预言:二三十年后,当中国的基础研究全面崛起,与美国、欧洲一起,共同勾勒人类基础研究的天际线时,其中的大多数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应该与自然基金委的资助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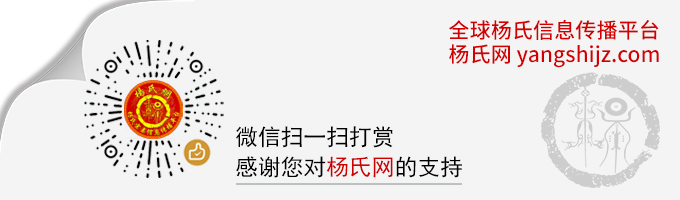
网站团队 |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服务条款 | 版权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