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榜 诗歌词赋 杨氏企业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西 广东 海南 湖南 湖北 江西 福建 四川 贵州 云南 浙江 江苏 河南 安徽 陕西 山西 山东 河北 辽宁 吉林 甘肃 青海 台湾 香港 澳门 新疆 宁夏 西藏 海外 黑龙江 内蒙古 |
学界有关宋代家族史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但大多集中于名宦、世家以及将门的研究[1],而关于宋代皇后家族的研究,笔者仅见香港何冠环先生的著作《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以及他一系列关于北宋外戚将门的论文[2]。然而,何先生的研究成果仅揭示了北宋,尤其是北宋前期后族的情况与特点,于南宋却未有涉及。南宋后族与北宋是很不一样的,起码从环境上来说,宋太祖与武将“与结婚姻”[3]的时代背景已经过去,北宋外戚一门几代担任武将,形成将门之家的景象也没有在南宋重新出现。南宋宁宗杨皇后的家族,可以说是南宋首屈一指的后族,因为他们在南宋中后期出现了两位太后和一位驸马,子孙后代“皆任通显”[4],发展极为迅速,且至南宋灭亡之际,荣宠不衰,故也可以说是南宋后族的典型代表。然而,这一家族本身形成的过程就迷雾重重,而其家族虽然壮大,但势力却难以企及汉唐后族,功勋也远远比不上北宋的外戚将门,这本身就说明了宋代后妃及外戚政治的一些特点。因此,把杨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可窥见南宋后族的特点,以及他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地位。
一、二杨并源
南宋宁宗杨皇后乃有宋一代著名的女政治家,她的政治作为,无论是诛杀韩侂胄,还是嘉定十七年(1224)帝位传承之事,都为她招来很多争议。而同样备受争议,甚至可谓扑朔迷离的,是她的籍贯和身世,因为不同的古籍有不同的记载,这也跟她早年的经历大有关系。能够比较确定的有两点,第一,她自幼入宫,母亲是宫中乐师,而她自己一直在高宗吴皇后身边侍奉,为“则剧孩儿”[5];第二,她有一个哥哥杨次山,后者家族也构成她的外戚。但不确定的也有几点,第一是她的籍贯,历来有上虞、遂安及川蜀之说。第二是她的姓氏,《宋史》其本传就说她“忘其姓氏”[6],后因认了杨次山当哥哥而姓杨。其三就是她跟杨次山的关系,《宋史·杨次山传》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认为他们是亲兄妹,《宋会要辑稿》以杨次山之父杨渐作为杨皇后的亲生父亲,也间接承认了这一点[7]。但其他材料也有不一的说法,如《宋史·杨皇后传》认为杨次山是杨氏后来认的哥哥;《四朝闻见录》则认为“后父即兄也”;《齐东野语》则云“遂得右庠生严陵杨次山以为侄”[8]。
以上诸点疑问中,杨皇后的籍贯问题是被探讨最多的,鲍绪先、何忠礼以及吴业国三位先生均有相关成果[9]。何、吴二文均据史料认为,杨皇后与 杨次山非亲生兄妹,且二人非来自同一地方。吴文认为,杨次山父子的籍贯“便是严州遂安县(今属浙江淳安县)无疑”,而杨皇后则有可能是蜀人;何文则以众多史料佐证,认为杨次山父子来自浙江上虞,而杨皇后则是严州遂安县人。何忠礼先生的文章论证最为严密,且论据充足,结论也最让人信服,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恐还略存误差。何文所据,乃李心传所记“今上杨皇后,遂安人也”[10],再佐以《景定严州续志》两条史料。然而,宁波出土的《宋杨惠罙墓志》指出杨皇后之侄孙女杨惠罙“世家严之淳安”[11]。墓志资料虽未必可以尽信,但子孙对于先人之籍贯断不会轻易弄错,且该墓志作于宋度宗咸淳年间,属于当时记录,这说明杨氏后人认为他们是淳安而非遂安人。当然,这两个地方是相邻的,后来遂安也并入淳安,故《景定严州续志》说“杨太后为严人”[12],也大体准确。
关于姓氏问题,何忠礼先生也有具体的考证,他认为所谓“忘其姓氏”是有违史实的,因为宋代宫女入宫非常严格,因此入宫前她们的姓氏、年龄均须注入名籍,而若连姓氏籍贯都没有的人,则属来历不明,不可能被宫廷接纳[13]。这一论证是非常有道理的,然而,按照《四朝闻见录》的记载,“(杨皇后)母张夫人以乐部被宪圣幸,后以病中归李氏”[14],其死后杨氏才被招入宫中,则她原来应该姓李才对。而《齐东野语》亦云“后初姓某”[15],与叶绍翁所载相呼应。如此,她若以李姓(或某姓)入宫,也算是有姓氏的。不过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何先生的结论依然是正确的。因为按照宋人习惯,他们最重本家之姓,就算随母改嫁,因而改姓,富贵后大多会恢复原姓。如北宋名臣范仲淹,母亲改嫁后曾改姓朱,进士及第后即复其原来之范姓[16]。再如孝宗皇后谢氏,微时曾“鞠于翟氏”,故以翟姓入宫,被立为后之后“复姓谢氏”[17]。故此,若杨氏果真本家姓李的话,她完全应该恢复李姓,并寻找李姓的戚属[18]。最终,杨皇后以杨氏为姓,即说明无论她是否“初姓某”,但她本家姓杨,此点当无疑问。如果《四朝闻见录》记载属实的话,李氏最多只是她继父的姓氏罢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杨氏一族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杨渐,究竟是何许人也?史书对杨渐所载不多,其中《宋史·杨次山传》曰:“(次山)曾祖全,以材武奋,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渐,以遗泽补官,仕东南,家于越之上虞。”[23]此处认为杨渐乃杨次山之祖父,而杨全则为其曾祖。但另据《宋杨惠罙墓志》记载,杨谷之女杨惠罙,“曾祖渐,赠太师尚书,今追封齐王;祖次山……”[24]而《宋会要辑稿》亦云杨皇后为“保义郎、累赠太师、尚书令、追封齐王渐之女”[25],墓志铭对于籍贯和祖先一般很少有误,而《宋会要》更是当时的档案,由此可知,杨渐必不可能是杨次山及杨皇后的祖辈,《宋史》所记应是笔误。如此,则剩下的问题是:杨渐究竟是杨次山还是杨皇后的生父?何文认为杨渐不可能是杨皇后的生父,理由是:“如果保义郎杨渐确为杨皇后的父或祖,那么其母张氏作为官宦人家的妻或媳,怎么会离夫别子进入宫内担任身份卑贱的‘乐部头’?年幼的杨氏又怎会孤身入宫作‘则剧孩儿’?”[2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官宦人家”的头衔是可以伪造的,且宋朝确实有过伪造的前科。宋真宗刘皇后出身卑微,她就为父亲刘通伪造了一个“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的头衔,从而冒认自己是太原刘氏的后人[27]。因此,杨皇后大可以效仿刘皇后,为自己出身低微的父祖伪造一个身份。然而,就这两个案例看,无论是刘皇后还是杨皇后,她们首先选择的并不是为家人伪造身份,而是想依附一个已知的大族。刘皇后是两次寻求依附都遭到拒绝,故才不得已进行伪造,但杨皇后却成功地找到杨次山。杨次山乃武学生出身,此时或已在御前带御器械,而其父杨渐也是“以遗泽补官,仕东南”[28],也就是说,父子二人均是官员。宋代对于官员的管理有非常严格的制度,故有所谓“官户”之称,能成为官员者,其姓名、籍贯、出身、经历等均会被一一记录在案。据《宋史》记载:“高宗建炎初,行都置吏部。时四选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诸州、府、军、监,条具属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历仕功过、举主、到罢月日,编而籍之。”[29]又据《宋史·高宗纪》,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诸州守贰考各县丁籍,依年格收除;民间市物,官户、势家与编氓均科”[30]。由此可见,即便乱离之日,南宋朝廷也不会让这一制度废弛。杨次山先入武学,继而为官,其父杨渐也是官员,其时南宋早已安定,故其家庭、籍贯当记录清楚,断难更改。因此,杨渐必定为杨次山生父无疑。
如此问题又出现了:杨渐若为杨次山之父,则杨皇后之生父又为何人?关于这一点,地方志上的史料也许能提供一些线索。严州地区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当属修订于南宋景定年间的《景定严州续志》,该志并没有提供有关杨皇后先人的任何信息,但却明确指出她是严州人[31]。此后,始编于洪武年间,而成书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明一统志》,明确表明杨皇后生父名杨宇,并指出他是从开封迁居而来的,其墓在淳安县南七十里。另一方面,该书把杨次山归为绍兴上虞人,更进一步说明他们两人并非同乡[32]。再后,《嘉靖淳安志》延续了《明一统志》的说法,但《万历严州府志》及《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均认为杨宇是杨皇后祖父,而杨纪才是杨皇后的父亲,并封永阳郡王[33]。那么,杨皇后的生父究竟是杨宇还是杨纪?杨纪是后来才出现在万历年间的志书上的,而且记载很有问题。第一,两部万历志书均说他的墓在“仁寿乡辽源巧坑”,而杨宇墓同样也在“县南七十里”的辽源巧坑,但前一条《童頵墓》则明确指出仁寿乡在县东二十里[34]。如果这只是地理考证失当的话,那说杨纪是永阳郡王就非常不合理了,因为杨次山作为后兄已经拜为永阳郡王,后父——如果杨皇后承认并追封的话——无论如何都应该比他高一等,如杨渐——杨皇后所认之父——就被追封为齐王。再者,根据周密记载,杨皇后“既贵”后,“耻其家微,阴有所遗,而绝不与通”[35]。既然绝不与通,就更不可能给生父封王,从而给后世留下话柄。另一方面,关于杨宇的记载出现较早,其被录入志书之年代,仅仅是杨皇后活跃时期的二百余年之后,而其流传,可能更早,故真实的可能性较大。故此,笔者认为,如《明一统志》及《嘉靖淳安县志》所言,杨皇后之生父是杨宇,似乎更为合理。据志书记载,他与杨次山的祖父杨全都是开封人,但后者却是战死开封,而他则南下逃难至淳安,也许这也是杨皇后选择杨次山家族作为其宗族的原因[36]。而他南逃难民的身份与杨皇后“家微”的记载也最相符合,且史料没有记载他有任何封爵,则又符合“绝不与通”的条件。
接下来就是认祖归宗了,但显然不是杨皇后,而是杨次山。杨次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虞杨氏,他也是来自开封的外来户,只因父亲“仕东南”,才“家于越之上虞”[37]。此时他既然与后宫杨氏相认,当然要改易籍贯,让自己的家族与杨皇后一样,成为淳安杨氏。这种改易,说明对于当时因战乱而南下的人来说并没有固定的故里,因为他们的根不在南方,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在南方某一个地方站稳脚跟。杨次山一家南下后,尽管还保持着官户的身份,但在遇到后宫杨氏之前,他们根本不能与早已扎根南方的世族相比,攀附后宫,徙族于淳安杨氏,乃他为家族设计的发展之道。由于之前的档案依然存在,故在史料上经常会出现他是上虞人或会稽人的说法。但史料有关他子孙的记载却大不一样了,据《景定严州续志》记载:
严为恭圣仁烈皇后毓庆之乡,后兄杨惠节王次山,字仲甫;后侄敏肃王谷,字声之;忠宪王石,字介之,每集必为统盟,其后节钺蝉联,缨绂辉映,率继先志。今节使蕃孙之子镇,以尚帝姬,益贵斯集,益有光焉。[38]
上述材料说明,从杨次山开始,杨家籍贯已迁至严州;而杨谷、杨石更曾出席当地乡会;其后杨谷之子杨蕃孙及孙杨镇,皆以严为乡。除此之外,同书卷七有云:“独高峰在常乐乡,嘉定间径山僧妙机为浮图,其上郡人杨缵书其扁。”[39]所谓杨缵者,即杨石之孙也。另《杨惠罙墓志铭》更云:“宋故广国夫人杨氏,讳惠罙,字德玉,世家严之淳安,赐第行在所,恭圣仁烈皇后侄孙女也。曾祖渐……”[40]说明在杨氏后人看来,从杨渐开始,他们就是严州人,而且其家在当时之淳安,而非李心传所说之遂安。这更进一步说明,至迟到他孙子那一代,杨次山家族的籍贯转换已经彻底完成。
这本是两个来自北方的杨姓家族,一个家境卑微,但却有女得宠于后宫;另一个虽属小官僚家庭,但却未及荣显。庆元年间,这两个家族联合一起,是各取所需,但从此又休戚与共。然而,这只是开始,当时杨氏还未被立为皇后,历史的走向还有很多种可能性,故他们的家族要获得更大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间还须经历一些风波。为了后族的利益,他们必须运用一些政治手段,制造一些政治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影响极其深远。
二、政治与家族
《宋史》杨次山本传云:“次山能避权势,不预国事,时论贤之。”其子杨石其后更是劝谏已垂帘听政的杨太后撤帘还政,而自己与兄长杨谷也韬光养晦,多次辞免朝廷所授之高官厚职[41]。于是,杨氏父子历来备受称道,堪称宋代外戚之典范。然而,作为外戚,他们更关心自身的既得利益,甚至是人身安危。所谓“能避权势,不预国事”,只是维护家族利益的手段而已。当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南宋后族与汉、唐后族的区别,后者一向主张垄断朝廷权力以维护家族利益,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与皇族争夺权力,于是站在皇帝角度而写成的史书,总是批评历代的“外戚之患”。后人对宋朝的后妃与外戚评价颇高,认为“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42]。这其实说明宋代的后妃与外戚政治比之前代已发生根本改变,外戚集团不再、也无力再与皇族——更具体是与皇帝争权,他们的利益已经与皇帝的利益挂钩——即便他们能扶持一个皇帝上台,但却无力控制一个已经上台的皇帝,反而要想方设法维护这个皇帝的权威。而后妃尽管能够在宫中参与政治,甚至代皇帝行使最高权力,但这只是一种专制皇权的让渡,而非贵族政治时代权力在不同家族之间的分享,故她们所赖以统治者,也不再是宫外的戚属,而是朝中大臣。对于外戚后族来说,他们最大的利益不再是政治权力,而是荣显的社会地位,以及数之不尽的财富。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在政治上就无所作为,相反,若朝廷大政涉及本身利益,他们也必奋起力争,有时候还会铤而走险。
杨氏家族发展的关键是杨皇后,如前所述,她的生父极有可能是从开封逃亡南方的难民,母亲张氏夫人也是宫中身份卑贱的乐师而已,而她自己,则由母亲带进皇宫,侍奉在高宗吴皇后身旁,为“则剧孩儿”[43]。宁宗尚是皇子时,就对杨氏特别关注,每次去参拜吴太后,“必目之”,有时甚至眼带异光(目后有异),后来他亲自请求吴太后把杨氏赐给他,吴太后也同意了[44]。宁宗即位后,于庆元二年(1196)三月封杨氏为平乐郡夫人,三年四月进封婕妤,五年五月进封婉仪,六年二月进位贵妃[45]。而大概就在庆元年间,她跟杨次山认为同宗。杨次山愿意跟杨氏认为兄妹,当然是想通过她来提升自己的官位,以及家族的地位,他确实因此从带御器械累迁至吉州刺史。然而,嫔妃再受皇帝宠遇,终究还是嫔妃而已,此时的杨家还离后族很远。而当时的皇后韩氏乃系出名门,来自北宋著名的安阳韩氏家族,其先祖是北宋名臣韩琦,而其叔祖则是当朝权臣韩侂胄,她本身也是宁宗在藩邸时的原配夫人,故其地位是不可撼动的[46]。
然而,命运之神在庆元六年(1200)开始眷顾杨氏,她当年二月被进为贵妃,而同年十一月七日,韩皇后崩于坤宁殿[47]。中壶虚位,宫中嫔妃中地位最高者就是这位杨贵妃了,只差一步,她即能够母仪天下。重新择后是皇帝与朝廷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然而,杨氏的皇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据《宋史》记载:
恭淑皇后崩,中宫未有所属,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48]
从这段史料可以分析出几个信息。首先,杨贵妃在后宫并非没有竞争者,曹美人就是她的对手。而且从文字看,曹美人在得宠方面并不输于杨贵妃,而是“俱有宠”。其次,杨贵妃此时并不受朝中权臣韩侂胄待见,后者是前皇后的叔祖,并因拥立之功,对皇帝很有影响力,且确实已经在怂恿皇帝立曹美人为后。还有一点这里没有提到的,至嘉泰二年(1202)立后之时,杨贵妃已经四十一岁了,年龄已大,姿色也肯定不复当年,更何况,她比宁宗还大六岁[49]。当然,杨贵妃还有她的优势,她酷爱读书,“颇涉书史,知古今”,说明她对历史有很深刻的见解,并能借古讽今。“性复机警”,足见她聪明伶俐;“任权术”,则说明她已经开始帮助宁宗解决政治问题。此外,她虽出身低微,但自幼以“则剧孩儿”的身份被养于宫中,这让她天然地熟知琴棋书画,精通诗词歌赋。有记载说她“能小王书”,宫中很多名画——尤其是著名画家马远所作之画——往往是她以“杨妹子”的身份在上面题诗的[50]。如此文采斐然又通晓古今的女子,难怪宁宗早年就已看中她,并一直对她宠爱有加。《宋史》认为,宁宗最后决定立杨氏为后,是因为她上述的种种优势。这些当然都是原因,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嘉泰二年(1202),杨贵妃有孕了,且为宁宗生了一个皇子。据李心传记载:“华冲穆王坰,上第五子也。母曰杨皇后。嘉泰二年冬生,未逾月薨。”而就在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杨氏被立为皇后[51]。史书未载皇子死于立后之前还是之后,但无论是皇子出生的欢庆,还是其薨逝的悲恸,都足以打动宁宗。
我们并不确定杨次山在立后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杨氏被立为皇后,杨家就一跃成为当朝后族。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据《宋史》记载,韩侂胄怂恿宁宗立曹美人的图谋,被杨次山的门客王梦龙告知了杨皇后。皇后知道此事后,“与次山欲因事诛侂胄”[52]。换言之,《宋史》认为杨皇后诛杀韩侂胄的原因,是对立后之事怀恨在心。然而,无论杨皇后如何怀恨,她已经是皇后了,若她深闺自守,远离政治,韩侂胄亦无奈之何。但她显然不能在政治上安守本分,她在宫中浸淫多年,遍读经史,后来更侍奉天子于左右,政治野心早已形成。而宁宗恰恰又是个“不慧而讷于言”[53]的人,这让她有了更大的权力空间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韩侂胄专政显然是她在政治上大展拳脚的障碍。虽然身处内宫,不能在朝堂上跟韩侂胄正面冲突,但由于宁宗“非心黄屋”[54],她总能掌控皇权,起码能左右宁宗的决策。而韩侂胄方面,竟“自置机速房于私第,甚者假作御笔,升黜将帅,事关机要,未尝奏禀,人莫敢言”[55],这相当于架空了宁宗的权力,也意味着剥夺了杨皇后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样一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年韩侂胄估计也是预见到这一点,才极力阻止立杨氏为后;而此时,杨皇后要除掉韩侂胄,也势在必行。另一方面,韩侂胄凭借其专擅国柄的势力,可谓气焰嚣张,不知收敛,这就更进一步得罪宫中的主事者杨皇后了。如叶绍翁记载,韩侂胄有妾谓“四夫人”者,“慈明(即杨皇后)尝诏入貌,赐坐以示优宠,四夫人者,即与慈明偶席,盖騃也,慈明心衔之”[56]。由此可知,杨皇后并非没有尝试向韩侂胄示好,但却实在不能容忍他及他家人的嚣张气焰。
宋代后族的势力已远不如汉、唐之时,而具体到杨氏一族而言,他们只是刚刚结合,在朝中还没有站稳脚跟。杨氏被立为皇后之后,杨次山也只是被从吉州刺史提升为福州观察使。故此,他们的家族利益尚需要朝中有力的大臣为他们实现。韩侂胄一来刚愎专横,二来他是高宗吴皇后的姨甥,以及前韩皇后的叔祖,其妻吴氏又是吴皇后的侄女,故其所代表的家族利益与杨氏不同,显然不是理想的合作者。据《齐东野语》记载,王梦龙得知韩侂胄图谋册立曹美人后,首先告知的是杨次山,其后杨次山转告杨皇后,“后由是生怨,始有谋侂胄之意矣”[57]。若杨次山有心躲避政治危机,他完全可以遮掩这一秘密,并韬光隐晦,远离朝廷政治,前韩皇后的父亲韩同卿就是这么做的[58]。但这样一来,杨氏一门的小日子也许还能继续过下去,但其长远发展必遭韩氏阻碍。故此,为了家族利益,他必须把这一秘密转告杨皇后,让她一来有所提防,二来也早作图谋。其后他更如《齐东野语》及《宋史·杨皇后传》所言,与皇后密谋诛韩之事,并内外联系,促成其谋,因为韩侂胄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利益的绊脚石。开禧北伐兵败如山,则成为这次阴谋的触发点。
当然,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一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就是皇子荣王赵曮。宁宗曾育有八子,但都夭折。在兖王去世之后,他接受宰相的建议,把宗室子弟赵与愿养于宫中,改名“曮”,至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受诛之时,他已经十六岁了[59]。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是宁宗唯一可能的继承人,无论是哪一方能争取到他的支持,胜算都会倍增。这一点,连韩侂胄的门客都意识到了。据元人刘一清记载,韩侂胄一门客曾指出他“危如叠卵”,其中两条理由是“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则皇子怨矣”,韩侂胄复问其计,其人答曰:“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间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徳寿,虽怨无能为矣。”[60]显然,这位门客的计谋,重点乃行禅让之法,拥立皇子赵曮为新君,从而架空杨皇后的权力。遗憾的是,韩侂胄并没有争取赵曮的支持,或许是他太过狂妄,又或许他根本与赵曮不和,无法争取。然而,宫中的杨皇后却是近水楼台,成功劝说赵曮加入自己的阵营,并让他首先给皇帝上书,请罢韩侂胄。罢免朝廷重臣,毕竟是国家大事,由皇子出面,合情合理,亦可免却后宫与外戚干政的骂名;而堂堂皇子身份,亦非韩侂胄轻易能够推倒的,这一方面无论是作为外戚的杨次山,或其他支持倒韩的朝中大臣,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事情并不顺利,宁宗对韩侂胄眷顾有加,即便杨皇后从旁赞襄,他也不肯就范。于是杨次山内联外结,联络朝中重臣图谋大事——这与“能避权势,不预国事”很不相符,而杨皇后则以御笔虎符,调遣禁中侍卫诛杀侂胄。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刻,宁宗甚至还想派人追截诛韩侍卫,杨皇后泣告曰:“他要废我与儿子。”[61]这种哭诉当然有夸张成分,但“儿子”一词,说明皇后与皇子已结成同盟:皇子非皇帝亲生,若有皇后认作亲儿,则子凭母贵;而皇后亲儿已逝,若能抚育皇子并使之成为太子,则她的地位会更加巩固。更重要的是,这位皇子将来有可能成为皇帝,如此,则杨氏家族之利益起码能再延续一代。
事实也是如此,韩侂胄被诛的最大受益者是皇子赵曮,他本来只是宁宗养子,诛韩后一举成为皇太子,并改名赵询[62]。若宁宗有所不讳,他便是唯一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当然,杨氏家族的受益并不比赵询少。杨皇后作为嫡母,已能有效控制赵询,从而得以从中预政。据叶绍翁记载,诛杀韩侂胄后,杨皇后“每遣景献谕时相,凡除授必先吴氏而后其家”[63]。此话所叙述者,当然是她感激吴皇后养育栽培之恩,但同样也反映出,她乃通过赵询给宰相传达自己的懿旨,从而干预政治。至于杨氏家族,当然大受封赏,杨次山授开府仪同三司,并于嘉定三年(1210)封少保、永阳郡王。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许奕与真德秀认为杨次山恩赏太重,宜只予其一,于是封还制书,引致杨皇后震怒[64]。这说明当时杨皇后的势力已足以左右朝廷封赏,以扩大自己的家族势力。当然,对杨次山来说,他要维持的家族利益是极尽荣宠的社会地位,而非如韩侂胄一样权倾朝野。三代封王足以满足他的虚荣,而前车之鉴,他并不想杨家的利益如韩氏一样,一朝丧尽,故此时他当然“能避权势,不预国事”了。但是,杨氏家族利益的保证来源于中宫的权力,但中宫毕竟不能走出外朝,而杨氏族人又不愿涉足权力,故他们需要一个外朝的代理人。太子的老师、参与了诛韩图谋的史弥远正是一位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与太子的关系更有利于宫内宫外的沟通,而他本人对皇后也是毕恭毕敬,对杨氏家族也照顾有加,就这样,他们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政治合作,而“每遣景献谕时相”,则是他们在赵询去世之前的合作模式。
中宫皇后主政,太子摄政,外朝宰相辅政,后族之家享尽荣华富贵,但却不插手权力,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政治平衡,宁宗一朝在这种平衡中安稳地度过了十三年。嘉定十二年(1219)杨次山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去世前,朝廷把他提升为会稽郡王,去世后又追封冀王[65],不但位极人臣,更能寿终正寝,这也正是他作为后族外戚所追求的人生。然而第二年,赵询在当了十三年太子之后,不幸薨逝[66],这让政局再起波澜。皇帝已经没有再生育了,故他和朝廷不得不重新选择宗子入继,以承大统。嘉定十四年(1221),宁宗下诏,以沂靖惠王嗣子赵贵和为皇子,改赐名“竑”[67]。太子薨逝,新皇子入继,打乱了杨氏家族的部署,毕竟他们与前太子相处十几年,双方已经建立起互信与互助的关系,而家族的长远利益在宁宗之后也能得到保障。此时新皇子入继,非其所立,脾性意向俱不所知,如何保证杨氏家族的利益,的确需要一番筹谋。此时杨次山早已离世,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杨皇后解决。皇后的办法,是把自己的侄孙女吴氏嫁给皇子,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皇后也是杨氏后人,如此一来,杨家的利益就能得到保障[68]。扶持亲信之人当皇后,从而控制后宫,以延续家族利益,这是宋代很多皇后的做法。如北宋之刘太后为仁宗选立郭氏,再如宁宗的前皇后韩氏,本身也是高宗吴皇后的外戚。然而,吴氏并没有在杨家与皇子之间沟通斡旋,相反,她的妒忌之行招致皇子的讨厌,夫妻关系非常糟糕。同一段材料认为,皇子不能处理好夫妻关系,并沉迷酒色,招致皇后的愤怒,成为他日后被废的原因。然而,冷落妻子、沉迷酒色可以让赵竑招致皇后的责骂,但却不足以让他们关系紧张,皇后是一位很谨慎的人,这种重大事情她必须再三衡量,才会作出决定。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驾崩,而此前,一场阴谋早已在酝酿。之前宁宗唯一的皇子被废为济王,而沂王宗子赵昀被迅速立为皇子,而后即位,是为理宗。有学者认为,这次阴谋依然是由杨皇后主导的[69],但各种史料均表明,丞相史弥远一直在暗中策划此事。如前所述,在诛韩事件后,史弥远被选中作为杨皇后在宫外的合作者。他跟中宫、太子及后族都有良好的关系,在此后的十三年间,他已成功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并在朝廷上独当一面,成为一代权臣。如果太子赵询不死,他这位老师必可安枕无忧,继续稳稳地坐在丞相的位置上。然而,新皇子跟他并无师生之谊,反而对他的专政非常厌恶,并立誓将来继位后要把他远贬岭南。史弥远惊惧异常,于是暗中让同乡郑清之培养沂王宗子赵昀,以备将来[70]。然而,按照宋朝的各种制度,丞相权力虽大,却无改立之权,且这种图谋不但需要一个可以当皇子的人选,更需要宫内宫外包括两制官员以及侍卫禁军的合作。能够协调这些官员的,只有天家代表——杨皇后。事实上,在之前的宋朝历史上,储位发生疑问时,皇后或太后往往能起一锤定音的作用。英宗、徽宗与宁宗之立,俱是如此[71]。故此,史弥远此时要发动代立政变,必须得到杨皇后的支持。
杨皇后当然是不喜欢赵竑的,甚至有可能连宁宗都不喜欢他,否则不会把他立为皇子三年,都不愿意建储[72]。如果赵竑此时是皇太子的话,史弥远的图谋就无法实现了。但即便如此,杨皇后对废赵竑而改立赵昀之事还是犹豫的,毕竟从道理上说,赵竑此时是唯一的皇子,也就是宁宗唯一可能的继承人,没有宁宗的旨意而改立他人,这跟谋逆无异。据《宋史》记载,即便史弥远遣杨次山之子杨谷和杨石七次往返宫中,杨皇后都没有同意。最终,杨氏兄弟说了一句:“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73]这句话似乎是史弥远通过杨氏兄弟之口对杨皇后的威胁,但细心品味,杨皇后并非一般妇孺,她不但聪明,而且通晓经史,并已参与政治多年,怎么会相信另立的皇子会“内外军民皆已归心”的鬼话。再说,宁宗驾崩后她就是太后了,按照宋朝家法,即便她此时不同意另立皇子,将来这位皇子就算真能成为皇帝,也不敢把她与她的家族如何[74]。其实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史弥远向杨皇后分析当时形势,并绑架杨氏家族的利益,真正“内外军民皆已归心”,且有可能会让“杨氏无噍类矣”的不是后来的理宗赵昀,而是赵竑。众所周知,赵竑是很讨厌史弥远的,这也是后者图谋废立的原因。然而,当时的史弥远无论在关系上还是利益上,都很难与杨皇后切割开来。据张端义记载:“天宝间,杨贵妃宠盛,安禄山、史思明之作乱,遂有杨安史之谣。嘉定间,杨太后、史丞相、安枢密亦有杨安史之谣,时异事异姓偶同耳。”[75]至少在时人看来,史丞相能够专政,是离不开杨皇后的支持的。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两人诡谲交通,淫乱后宫,于是写诗讽刺曰:“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蒙。”不管这是否谣言,皇子赵竑早就听在耳里,且对于“杨后之事,济王嫉之”[76]所谓“杨氏无噍类”,应该是指他上台后会对杨氏进行清算,这样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诚然,史弥远的话是有夸张成分的,因为赵竑未必就“内外军民皆已归心”,且按照宋朝的政治环境,估计他也不敢让“杨氏无噍类”。但单从政治而言,济王要除掉史弥远,就必先架空杨皇后的权力,故若由赵竑继位,杨氏家族的利益必然受损。新皇帝即便不能处置太后及其家族,但眷顾之情肯定不如往昔,甚至有可能把他们边缘化,那在太后去世之后,杨氏一族就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了。故此,皇后再三权衡之后,也只有同意废立之事,以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此后,程珌草遗诏改立赵昀,夏震奉旨押送赵竑,都是出自杨皇后的懿旨,也只有她有权威来调动这些朝中文武来配合这场宫廷政变。第二年发生湖州之变,赵竑是注定要死的,因为他不死,皇帝、太后和丞相及他们家族的利益都不能得到保障,这也是为什么长久以来理宗不肯为赵竑平反的原因——他们三家早就坐在一条船上了[77]。
新君即位,太后垂帘听政,这一方面是史弥远欲借太后权威保扶理宗,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他们共同分享政变的成果。杨谷、杨石兄弟也分别被封为新安郡王与永宁郡王,此正如真德秀所言“稽诸典故,所未前闻”[78]。但他们很清楚现在的情况与往时不同,杨石即认为:
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由抚育,军国重事有所未谙,则母后临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悦服,虽圣孝天通,然不早复政,得无基小人离间之嫌乎?
他于是上书太后,论及汉、唐母后临朝称制的得失,不久,太后即撤帘还政[79]。从上引文段可以看出,杨氏兄弟深知此时之形势不仅与仁、英、哲三朝之初不同,且与当初太子赵询在生之时也不同。当初皇后对太子赵询有养育之恩,故太子能对她言听计从。但如今之皇帝,虽由杨太后拥立定策,但其教育成长,乃史弥远为之。且皇帝现已成年,太后若过多干预政事,只会令皇帝反感,从而有损杨氏家族的利益。所以,为保杨氏一族盛宠不衰,太后应让出权力,颐养天年,而杨氏族人则远避权势,以保富贵。为此,他们还搬离京师,远离这个天下权力所集中的地方。此外,他们还多次辞免朝廷的封赏,以向朝廷表明,他们后族杨氏,对皇帝并无威胁。
杨太后听从杨氏兄弟的劝告,交出最高权力,理宗感激她的定策之恩,对她极为尊崇,多次给她加封尊号,并在她七十大寿时率百官同朝慈明殿[80]。然而,同样是为了家族利益,她并没有放弃对理宗的控制,方法还是扶植自己的亲信之人,使其成为皇后。这一次她没有选宗族女子,而是选了宁宗朝的老宰相,曾经在宁宗立后之时给她施以援手的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据《宋史》记载,谢道清样子并不好看,且有一只眼睛失明,理宗本想立贾涉之女,年轻美貌的贾氏为后,但在杨太后的坚持下,他最终同意立谢氏为后[81]。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太后这一部署,对整个杨氏家族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在关键时刻,谢皇后将会出手帮助杨氏。另一方面,杨家虽然远避权势,但他们还是决定跟权势之家结为姻亲,以作为家族利益的保障。杨谷之女杨惠罙后来嫁给了史弥远的侄孙史茂卿,尽管当时史弥远已经去世,但史氏乃是明州的世家大族,终宋一代荣宠不衰,跟他们结合对杨氏来说非常有利[82]。身为外戚而联姻权势之家,这跟宋仁宗朝刘太后的外戚钱惟演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钱惟演一直谋求相位,最终虽不算身败名裂,但却郁不得志[83]。而杨氏家族所谋求者,只乃富贵、荣誉与社会地位而已。事实上,他们确实得到了这些东西,成为南宋中后期最大的后族,且一直延续到宋朝灭亡。
[1]比较著名的有戴仁柱著,刘广丰、惠冬译:《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张邦炜:《宋代盐泉苏氏剖析》、《宋代时期仁寿——崇仁虞氏家族研究》,载氏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304页、第305-345页。
[2]何冠环先生关于宋代外戚将门的研究文章有:《北宋外戚将门陈州宛丘符氏考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北宋外戚将门开封浚仪石氏第三代传人石元孙事迹考述》,《新亚学报》第30卷(2012年);《北宋保州保塞外戚将门刘氏事迹考》,《新亚学报》第31卷(2013年)。
[3]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杯酒释兵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页。
[4]脱脱:《宋史》卷243《杨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58页。
[5]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111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5页。
[6]《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
[7]见《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5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太后》,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27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25页。
[8]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111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
[9]见鲍绪先:《浙江淳安发现宋恭圣仁烈杨太后家族宗谱及其墓地——宋宁宗杨皇后与宋度宗杨淑妃生平及其家族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4期;何忠礼:《南宋杨皇后姓氏、籍贯考》,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41-546页;吴业国:《南宋宁宗杨皇后籍贯、身世献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
[1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太后》,第527页。
[11]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
[12]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1《户口》,中华方志丛书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0页a。
[13]见何氏前揭文。
[1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页。
[15]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
[16]见《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67页。
[17]《宋史》卷243《谢皇后传》,第8652页。更详尽的记载,可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成恭夏皇后太皇谢皇后》,第38页。
[18]宋代后妃因出身卑微而寻找同姓贵族为亲族者并非自杨皇后始,北宋真宗刘皇后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她被立为皇后之后,曾多次寻找刘姓世族欲认为亲戚,但没有成功,后来还是让其从前的监护人龚美改姓刘,以作戚属。可见,宋代后妃对本家之姓非常重视,断不会找一个与自己不同姓的家族来移船就岸,从而改易自己姓氏,从刘皇后的案例看,就算要改,也是其他人改用皇后的姓氏。参见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载氏著《宋代婚姻与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3-264页;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载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285页。
[19]笔者并未亲见《宏农杨氏宗谱》,故本文所引该宗谱之内容,均为鲍文所载。
[20]浙江萧山县境内确实有一座山叫杨岐山,据说因杨渐及杨次山之墓在此而得名。见邹勷、聂世棠等:《萧山县志》卷14《陵墓》,中华方志丛书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58页;
[21]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8页。
[22]见《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6页。
[23]《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5页。
[24]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324页。
[2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第225页。
[26]见何氏前揭文。
[27]见《宋史》卷242,《刘皇后传》,第8612页。张邦炜先生经考证后,认为刘皇后“不是太原刘氏之破落户,而是太原刘氏之假冒牌。”见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
[28]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太后》,第527页;《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5页。
[29]《宋史》卷158《选举四》,第3712页。
[30]《宋史》卷31,《高宗八》,第585-586页。
[31]见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1《户口》,第10页a。
[32]见李贤等编:《明一统志》卷41《严州府》;卷45《绍兴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史部第230册,第1013页、第1072页。
[33]见姚鸣鸾等:《嘉靖淳安县志》卷7《塚墓》,影印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第16页a。杨守仁等:《万历严州府志》卷5《祠墓》,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杨守仁等:《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5《祠墓》,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34]见杨守仁等:《万历严州府志》卷5《祠墓》,第116页。
[35]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
[36]当时南方其实还有比杨次山家族更出名的杨姓大族,如福建明溪杨氏(著名理学家杨时之家族)和浙江慈溪杨氏(陆九渊弟子杨简之家族)。
[37]《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5页。
[38]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3《乡会》,第14页b-15页a。
[39]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7《桐庐县》,第5页a。
[40]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324页。
[41]见《宋史》卷465,《杨次山传附杨石传》,第13596-13597页。
[42]《宋史》卷242《后妃传·序》,第8606页。
[43]关于杨氏如何入宫,《宋史》其本传云其“以姿容选入宫”;《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则云其“少入慈福宫”,但未提供具体过程;《四朝闻见录》则认为是其母张氏死后,高宗吴皇后怀念她,乃把她的女儿招进宫中,时年十一二岁;《齐东野语》则云其母被招进慈福宫当乐部头,把她带进去的。笔者认为,她应该是由母亲张氏带入宫中的。明人毛晋所辑之《二家宫词》,记录了杨皇后宫词五十首,当然,其中或有一些伪作。当中有一首云:“阿姊携侬近紫薇,蕊官承宠斗芳菲。”四库馆臣据“阿姊”一词认为,这首诗当为杨皇后之妹杨妹子所作。杨妹子是否真有其人,历来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并不存在这个人物,详见下文注释。明人方以智所著《通雅》云:“江南呼母曰‘阿姐’。”而宋代史料亦有记载,宋高宗曾呼其生母韦贤妃为“大姐姐”。故此处之“阿姊”,所指者应是母亲。而“阿姊携侬近紫薇”一句,即说明是母亲张氏夫人把她带入宫中的,反过来,这也说明这首宫词应为杨皇后所作无疑。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太后》,第527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第60页;丙集《慈明》,第110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毛晋:《二家宫词》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355册,第713页;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89,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216页;方以智:《通雅》卷19《称谓》,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5页a。
[44]见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第175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页。
[45]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第225页。
[46]见《宋史》卷243《韩皇后传》,第8656页。
[47]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第225页。
[48]《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
[49]如前所述,杨氏生于绍兴三十一年(1162),而宁宗则生于乾道四年(1168)。宁宗生辰见《宋史》卷37《宁宗一》,第713页。
[50]杨氏能诗,可从其宫词中看出。当然,有学者邵育欣女士认为,所谓《二家宫词》,并非杨氏所作,乃后人伪作之。笔者认为其判断理据不足,但限于篇幅,在此不予辨证,当另文与之商榷。杨妹子的身份历来存疑,盖因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提出,其题马远画之诗,“往往诗意关涉情思”,非皇家气度,不似皇后所作。对这种观点,启功与江兆申两位先生已行辨证,认为杨妹子即是杨皇后。此外,在明朝一些收藏家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杨妹子”身份的怀疑或看法。如汪砢玉写道:“杨娃为宁宗后之女弟,故称妹子,以艺文供奉内庭,凡颁赐贵戚画,必命娃题署,故称大知阁。然印文擅用坤卦,人讥其僣越。”汪氏虽认为杨妹子乃杨皇后之妹,但他注意到其印文用坤卦,所谓坤卦者,母仪之象也。汪氏据此认为杨妹子实属僭越,但若杨妹子即是皇后本人,印文的使用就合情合理了。另庄泉曾写有《马远画删去杨妹子题愳庵以余为俗》一诗,最后六句云:“九皋看馬将無同,岂在牡牝玄黄中。看画且须论画外,妇人软语徒匆匆。牝鸡晨鸣家国丑,老夫此眼真俗否。”庄泉在这里是批评以女子之身而擅国政者,则此人必是杨皇后而非其妹。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页;陶宗仪:《书史会要》卷6,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99页;汪砢玉:《珊瑚网·画录》卷19《杨妹子画菊花并题》,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226页;庄泉:《定山集》卷1《马远画删去杨妹子题愳庵以余为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93册,第152页;邵育欣:《<杨太后宫词>辨伪》,《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启功:《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载氏著《启功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8-155页;江兆申:《杨妹子》,载氏著《双溪读画随笔》,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10-26页。
[51]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华冲穆王》,第529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九,第225页。
[52]《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6页。
[53]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第191页。
[54]刘一清著,王瑞来校笺考原:《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2《韩平原客》,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8页。
[55]《宋史》卷474《韩侂胄传》,第13775页。
[56]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四夫人》,第189页。另《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云:“侂胄既贵,四婢张、王、谭、陈皆有宠,累封至郡国夫人,所谓‘四夫人’也。每内宴,往往宣押与妃嫔杂坐,恃势骄倨,掖庭皆恶之。”如是,则韩侂胄嚣张之妾非止一人。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6页。
[57]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第45-46页。这个记载其实比宋史所载更为合理,因为作为门客,王梦龙没理由不先告诉东主而径行告知皇后;其次,他也没有直接面见皇后的机会。
[58]见《宋史》卷243《韩皇后传》,第8656页。
[59]见《宋史》卷246《赵询传》,第8734-8735页。
[60]刘一清著,王瑞来校笺考原:《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2《韩平原客》,第57-58页。其谋尚有其他部分,主要是让韩侂胄拥立新君后,招贤纳士,然后急流勇退。
[61]见周密:《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第47-49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第91-92页。
[62]见《宋史》卷246《赵询传》,第8735页。
[63]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第110页。
[64]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真文忠居玉堂》,第72页。
[65]见《宋史》卷465《杨次山传》,第13596页。
[66]见《宋史》卷246《赵询传》,第8735页。
[67]见《宋史全文》卷30,嘉定十四年六月丙寅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18页。
[68]见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济王致祸》,第87页。
[69]见戴仁柱著,刘广丰、惠冬译:《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第四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70]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5-8736页。
[71]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页;曾布:《曾公遗录》卷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211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宪圣拥立》,第12页;周密:《齐东野语》卷3《绍熙内禅》,第71页;刘广丰:《宋代后妃与帝位传承》,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
[72]反过来,赵竑本身对宁宗夫妇也没有多少感情。在宁宗驾崩后,他并没有悲声痛哭,反而站在门前“跂足以需宣召”,与之前入继皇位的宗子举动大不相同,似乎在他看来,皇位已经到手了。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6页。
[73]所谓七次往返之事,未必存在,但“杨氏无噍类矣”之语,应该是通过某种渠道传达给杨皇后的。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7页。
[74]真宗即位前,太宗李皇后曾欲发动政变改立元佐;而高宗时,吴皇后也不主张立赵昚为储。但此后这两位皇帝即位后,都没有清算嫡母,反而尊之为太后。最离谱的是太宗对待太祖宋皇后的做法,但也只不过让她丧不成礼而已,其生前一直保持“开宝皇后”的称号。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至道三年三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62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1《高宗立储》,第201页;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7,第64页。
[75]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页。
[76]刘一清著,王瑞来校笺考原:《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2《史弥远》,第72页。
[77]见《宋史》卷246《赵竑传》,第8736-8738页;卷422,《程珌传》,第12616-12617页;周密:《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第252-259页。
[78]《宋史全文》卷31,宝庆元年十一月乙丑条、丙寅条,第2142页。
[79]见《宋史》卷465《杨石传》,第13596-13597页。
[80]见《宋史》卷243《杨皇后传》,第8658页。
[81]见《宋史》卷243《谢皇后传》,第8658-8659页。
[82]《宋杨惠罙墓志》指出,杨惠罙生于嘉定十四年(1221)九月,“及笄,归于我大父通判架阁”,亦即十五岁出嫁,其时为端平二年(1235),而史弥远则卒于绍定六年(1233)。此外,据《宋史茂卿墓志》记载,杨氏乃是继室,而杨氏在端平二年(1235)时也已被封为荣国夫人,这是外命妇中除宗室女子外的最高等级,相对于当时只是六品承直郎的史茂卿,她算是下嫁了。见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283-284页;第324-325页。
[83]见《宋史》卷《钱惟演传》,第10341页。
本文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原文16000字。推送版为作者有所增补,全文约27000字,引用时请注明出处。若涉侵权,请联系删除。感谢刘广丰先生赐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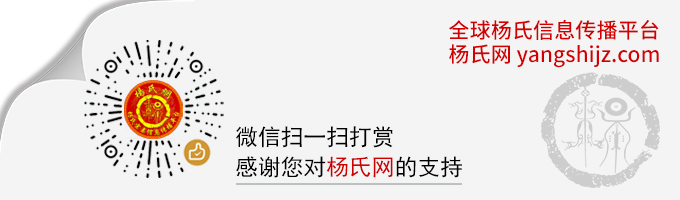
网站团队 |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服务条款 | 版权声明